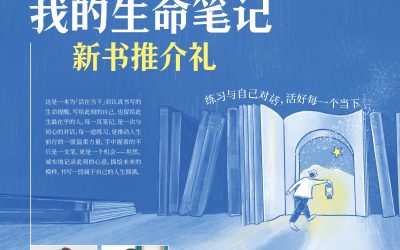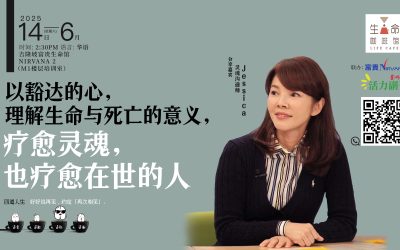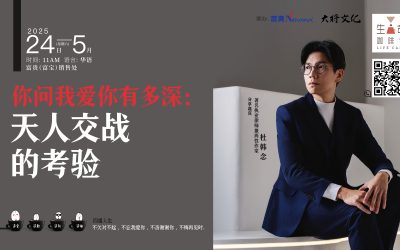阿嫲的长命百岁
/黄爱玲 – 富贵关怀文化礼仪管理部
星期日晚11点半,是该就寝准备隔天上班的时间,接到了姐姐的简讯:“阿嫲身体很弱,心跳只剩44,大家做好准备。”当下,第一个蹦出的想法不是“希望阿嫲可以熬过这关”,而是“阿嫲终于可以离开了吗?我希望她走”。
阿嫲已经90几岁,约10年前开始身体健康就每况愈下。跟很多老人一样,不过是跌了一跤,动了一次手术,余生就只能在轮椅上渡过了。慢慢地,阿嫲不再需要坐轮椅,不是因为情况好转,而是她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终日躺卧在床上。每日坐起的时间只有在洗澡和喂食的时候。

“皮包骨”过去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尤其青春期流行的“瘦就是美”时尚,总是用来形容那些身形让人嫉妒的女生。曾经,“我也好想皮包骨哦”。直到,在阿嫲身上见证到真正的皮包骨。不要说脂肪,但凡能在阿嫲的身上摸到一丝肉的触感,都能勉强感受到她的生命仍在持续,然而这都是奢侈的。
还有“鸡皮鹤发”。鸡皮都比阿嫲的皮肤好。每次摸她,都感受不到正常人该有的体温。皱纹,松垮,没有弹性已经不是问题,还容易受伤,经不起稍微的挤压和碰撞。只要不留神,阿嫲的皮肤就会因为睡姿或自己抓痒而出现大片淤血甚至破皮溃烂的情况。
失禁,却又常因为营养摄取不足导致便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为缺水缺营养的虚弱而需要到医院打点滴……然后又回到家里,继续躺在床上,不断轮回。
我不确定阿嫲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因为她几年前就失智了。所以照顾她变得更难。她不知道不吃不喝对自己不好,不知道大力抓痒会弄伤自己;或许知道,只是没有多余的心力去顾及。她已经不认得人,任何人的靠近都会让她觉得没有安全感,不止会拒绝照顾,还会对照顾者打骂。

我回了姐姐的简讯,第一次鼓起勇气说了真心话。姐姐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反驳。有这想法的应该不止我,只是我是家里唯一敢指出房间里有一头大象的人。
不止我家人,相信很多照顾者都有同样的经验和感受。真话不能随便说,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背上不孝的罪名。中华传统最强调孝道,百善孝为先。但到底“孝”是什么?这个“孝”背后与社会结构和运行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久病床前无孝子” 是在感叹多数的子女很难长期坚持对久病父母的照顾,所以,它真正的意思是“无论任何情况,子女都应该(必须)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这是一块沉重大石,压在很多子孙的身上。有多少人敢理直气壮地对外宣称,他/她不想当这样的孝子/孝女?
在现今的时代语境下,这句话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一、对照顾者的道德绑架;二、把照顾责任外判于个体,忽视集体社会责任;三、对安宁疗护的缺乏认识。
在普遍照顾者是亲人的情况下,社会对于“亲情”的过度美化和期许,很多时候都会形成一种道德绑架。前几年在香港读书时,那里连续发生了几宗照顾者不堪长期压力杀死照顾对象的例子,包括了夫杀妻、子弑母、或父杀子的情况,加深了我对照顾者需求的关注。社会允许病床前的孝子/女有拒绝照顾的权利吗?哪怕照顾了,社会可以体谅他们也会疲累、有情绪吗?当年讨论是否把阿嫲安置在养老院时,爸爸第一个反应是“让人家知道我把妈妈送老人院会怎么看我?”多少子女在这个问题的考量上会先重视旁人观感多于父母和自己的实际需求?

社会普遍的善心会用在无家人的孤儿或老人身上,只要得知对方有家庭就会很常先质问“为什么家人没有照顾?”反映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习惯性把照顾责任单一归诸于个别家庭身上。但我们都有缴税的义务,需要在社会/工作岗位上付出,共同维持社会的秩序运行。哪怕是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没有在“工作”的家庭主妇,也因为培育和照顾子女而为社会延续生命和提供人力资源。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需要对社会负责,那为什么社会却不需要对个人的晚年或病患负责?凭什么照顾的责任只由亲人承担呢?现有的政府组织或民间机构,在这方面的资源少得可怜。久病床前本来就不该“只有”孝子。
而且,久病床前也不该只有“照顾者”这个选项。不久前,我给大学老师的母亲和室友的姑姑主持了丧礼。老师在追思文中透露,母亲身前曾表示不希望自己在久病卧床的情况下离世;室友说姑姑得知自己癌症末期后,很快就决定放弃只会延续她痛苦的无效治疗。若不是阿嫲已失去沟通能力,我这几年最想问她的是“你想这样继续下去吗?”相较于无限轮回的抢救和苟延残喘,或许阿嫲更需要的是安宁疗护——在各种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协助下缓解末期老人或病患的各种不适症状,尽可能让他们在无痛、舒适、尊严的情况下回归「自然死」(allow natural death)的过程。暂且不论我国在安宁疗护资源的严重欠缺,在社会普遍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子女们要提出这个想法都要面对很大社会压力。
星期一上班的路上,妈妈发来简讯,说阿嫲情况稳定下来了。我没有因此松了一口气,反而更沉重了。我不要阿嫲长命百岁,只希望她可以舒服且有尊严地离开。
富贵关怀礼仪与文化管理部
钻研中华文化对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与发展,着重于社会殡葬文化的始源,从古文化借鉴及演变;从而滋养富贵殡葬服务的发展、耕耘、深耕及拓展。
作者简介
黄爱玲,富贵关怀礼仪与文化管理部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中文系硕士,多年写作与研究经验。现为报章专栏作者,长年于港台网路平台发表文章。
《我的生命笔记》推介礼
这是一本为「活在当下」而认真书写的生命提醒。写给此刻的自己,也留给此生最在乎的人。每一页笔记,是一次与初心的对话;每一道练习,是推动人生前行的一股温柔力量。手中握着的不只是一支笔,更是一个机会——坦然、诚实地记录此刻的心意,描绘未来的模样,书写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圆满。
以豁达的心,理解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疗愈灵魂,也疗愈在世的人
在理解人生终点的过程中,我们不只是疗愈逝者的灵魂,更是抚慰生者的心。透过情感、信仰与爱的连结,本次分享会希望为在场的人带来一份平静与释怀的力量。
「富与AI」:科技与爱的踏脚石
科技本身并不排斥任何年龄,真正设下门槛的,倒是我们对自己的设限。只要愿意,我们依然能用双手去触碰未来,用好奇心重新认识世界。正因如此,富贵集团顺应时代所推出「富与AI」的附加服务。若干人或许仅仅认为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看似取代传统的告别仪式,可却能够回应现代人内心深处那份再爱一次的渴望。
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別
在关系里,我们常常以为来日方长,却忽略了有些话,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机会说出口。看似简单的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却是人这一生最难练习的功课。藏在日常的沉默中,躲在关系的缝隙里,但一直都在轻轻提醒我们:有些感情,值得更及时地表达。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天人交战的考验
当情义与私欲交锋,我们又该如何抉择?种种考验,无一不是在剖开人性最真实的模样。唯有守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珍贵,才能在纷杂中不失方向,而爱,始终是那道最清晰的答案。
AI虚拟分身告别式|「富与AI」弥补遗憾的缺口
然而,现实往往未能如愿。时间来不及、距离太遥远、病况突变,这些无法掌控的因素使我们错过了最后一次的拥抱,来不及听见微颤的再见……于是,未说出口的千言万语就像藏在心口的千刀万剐,一句不说,却句句作痛。每当想起,仿佛整个灵魂都被回忆凌迟,只能在漫漫长夜里反复咀嚼那些来不及说的爱与道别。
也正因为如此,富贵集团推出全马首创的AI告别式服务——「富与AI」,此服务目前率先于吉隆坡与雪兰莪地区推出,并作为传统殡仪配套的附加选择。
科技让告别值得回忆——「富与AI」开启殡葬服务新纪元
AI重建影像可协助家属释怀,特别是重症离世或是癌患家属。病榻缠绵多年,逝者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常常是在痛苦中挣扎求生。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生命以最脆弱的姿态缓缓谢幕。对家属而言,留下的最后画面,往往是无力与心碎。如今「富与AI」重建逝者影像,回到健康、有精神的模样,他们再一次张口说话,不带痛楚、不带病容,只带着柔和的声音,缓缓说出想留给亲人的那句:“别担心,我很好。”
生死别离后,我该拿什么爱你?——如何利益已亡故亲人
妙开法师表示,佛教认为,对亡故者最好的做法就是为亡故者诵经及持咒语回向,借由佛力加持, 将能让亡者受食。“至于要念什么经文或持什么咒,只要诚心与专注念佛号,所有功德亡故者都能收到。最简单的回向佛号就是:阿弥陀佛。其实在佛的世界是相通的,有分别的是我们,所有只要诚心,任何佛号都可以的。”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如果可以重来,我会如何?
有人说,人生最遗憾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来不及说的那一句话。及时,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深情。本次分享会将引领我们一起找回表达爱的勇气。
富贵集团慷慨捐赠百万善款予慈济 助力缅甸灾后重建
成立35年,富贵集团始终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包括在2015年尼泊尔发生7.8级强震时共捐赠了超过1000万令吉善款作为赈灾以及灾后重建基金;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捐赠总值800万令吉的医疗配备、物资、干粮和口罩等携手全民对抗疫情;今年初也捐赠50万令吉助力砂拉越水灾救援行动,提供所能之援。